奔向多年向往一游的地方——西藏塔尔寺
发布时间:2024-10-01 01:44:34作者:心经原文网3月25日,北京虽然阴雨,但丝毫没有令气网难耐的“桑拿天”得以改善。到了西藏就好啦,那里肯定凉快。”在去西客站的路上我这样安慰自己。一身热汗,行囊里却塞着厚厚的羽绒服。这一天是星期六。经过数月的准备和焦急的等待,今天终于登上了西行的列车。早8点50分整,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,我们“西天取经”之行开始了。同行的是两位摄影家:朱恩光和姜平。行李又多又重,除了尽量压缩的日常用品之外,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二百个胶卷、一个摄影箱和一个沉重的大脚架。
次日下午5点半,火车到达西宁站。在列车上我们与临铺的两位年轻的地理教师交上了朋友。他们在西宁有人接应,因而我们也就有了接应。运气不错,刚一出站,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直接给我们拉到当日的宿处—西宁大厦。接待我们的是解放军某部营房质检处的樊麦虎处长,由于他在某工地的指挥部当头儿,大家都称呼他“樊指挥”。下火车立即感受到了高原的气息,阳光那叫一个亮,空气那叫一个爽樊指挥让我们赶紧换上长衣服,以免着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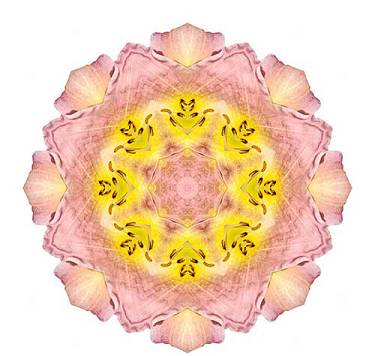
大约150年前,一位叫古伯察的法国神父,在环游中国的途中曾在塔尔寺逗留了三个月,留下了大量有关塔尔寺的翔实记载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夜间举行的一次法事活动。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见到如此奇特的宗教仪式了,古伯察的记述非常生动,空灵而神秘:“我们觉得似乎在梦中听到长空中一种如同是人数众多的合奏曲,这种混乱而无一定之规的声音慢慢地变得强大而清楚了。我们醒来之后,确实听到了喇嘛们祈祷的歌声。院子中由—种似乎是来自上空的灯光的微弱映影所照亮。一架梯子正好靠在墙上,我们飞快地攀登阶梯并立即就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。所有住宅的平屋顶上都由挂在长杆上的红色的灯笼照亮。全部喇嘛都穿上他们的礼服并头戴黄色法冠,坐在其住宅的平房顶上,用缓慢而单调的声音唱经。
这些无数的灯笼及其淡红色和光怪陆离的微光,被摇曳的反射灯光若明若暗地照耀着的喇嘛寺的建筑,这4000人发出的直冲云霄的宏亮的交响乐,再加上不断听到的唢呐和海螺号声,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隆重,并使人们心里感到了可怕的茫然和不知所措。平房顶上祈祷的喇嘛们的诵经声停止了,唢呐、钟铃、法鼓和海螺声分别三次骤然间响起。仪式结束了。灯笼熄灭了,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
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产物,遍及所有存在人群的地方。在漫长久远的历史长河中,人类需要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来支撑着自己去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,去和困难抗争。我们就要进入藏传怫教弥漫的地区了。藏族大多数人信教,我曾经试图了解一点藏传佛教,然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。
“到了,这就是塔尔寺。”樊指挥一句话将我从遐想中惊醒。汽车停在一个条石铺就的广场上。广场边一排白塔肃穆端庄,像是拱卫寺庙的挺胸腆肚的武士。塔尔寺是藏区黄教的六大名寺之一,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。寺內矗立着埋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遗物的圣塔。这里鲜明的藏域特色和浓郁的藏族风情使我们十分兴奋,禁不住端起相机连连拍摄。在许多禁止照相之处亦伺机偷拍。也许是神灵有验,立刻就有了报应。当一个胶卷拍摄完后,照相机自动倒片尚未完成的时候,我就急火火地打开了相机的后盖想换胶卷,估计要报废好几张底片。
塔尔寺的酥油花最为著名。在个独立的佛殿内陈列着许多的酥油花作品,姰丽多彩,栩枧如生。酥油花是藏族特有的艺术形式,其主要材料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。在酥油内调入各色颜料后,塑造成花鸟人物的形象。在塔尔寺每年都有酥油花节,不过由于酥油遇热就会变软融化,所以都是在较寒冷的季节举行。没想到在这7月的夏季也能够一睹酥油花的奇异。这一来要感谢青海凉爽的气候,二来还得归功于喇嘛们的维护。佛殿屋高顶厚,还围挂了遮阳的帐幔。即使在正午的阳光下,佛殿内也会凉气沁人。来拜庙的藏民很多。这还是平常曰子,樊指挥说,若是逢年过节,这里是人山人海,香客如云。



